
30载后的2019年5月仍在中国美术馆
1989年5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陶博吾书画展”,由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林散之作序,启功题写展名。展出陶博吾先生各个时期书画作品120幅,受到周谷城、李可染、启功等著名人士以及外国友人的高度评价。

(1989年5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陶博吾诗书画展期间,陶博吾先生与启功先生亲切交谈)
启功先生参观画展览时说:“陶老一生坎坷,但又长寿,每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诗,又写得好,这一点谁也比不了他,《满江红》这首词可以拿桂冠;石鼓文、散氏盘铭文写得好,就功力来讲,达到了吴昌硕水平,就夸张变形、生动趣味方面看,超过了吴昌硕!”

(陶博吾先生与李可染先生合影)
李可染先生参观时谈道:“陶老的诗写得好,田园诗有陶渊明的飘逸,抗战和文革中写的诗,又有老杜的深沉。行书对联结体奇特,个性强,又有趣味;篆书功力深厚,不在吴缶老之下;画学吴昌硕、黄宾虹,又跳出吴、黄。……如果我身体好,我会看上一整天,我要向你学习,你是我的学兄……”
整整30载后的2019年,又值北京的初夏,5月23日至6月2日仍在中国美术馆,将有50余幅陶博吾先生的真迹,将静候着各位旧雨新知。
布衣大师陶博吾生平

陶博吾(1900——1996),名文,字博吾,别署“栗里后人”、“白湖散人”等,江西彭泽人。
1925年考入南京美专,从沈溪桥、梁公约、谢公展诸先生学习书画。1929年考入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师从黄宾虹、王一亭、潘天寿、诸闻韵、贺天健、张善孖、王个簃、诸乐三诸先生学习书画,从曹拙巢先生学习诗词。抗战起携眷逃亡,由原省教育厅分发到吉安中学任国文教员,后又转入樟树中学。解放后,任南昌一联中和南昌十中语文教师。
其诗、书、画造诣皆深,书法绘画沉雄厚重、古傲拙朴、奇异生动,诗文情感真挚、意境超远。
其真、草、隶、篆四书皆精,尤以大篆、行书成就最为突出。其行书,纯真自然,无拘无束,不假雕饰、稚拙天真。其篆书,得力于散氏盘和石鼓文,初受吴昌硕影响,终成自家面目。
陶博吾平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习篆一径》、《石鼓文集联》、《散氏盘铭集联》、《博吾诗存》、《博吾联存》、《博吾诗词选》、《题画诗抄》、《博吾随笔》等,大部分著作已结集出版。

百年孤独——《陶博吾书画集序》
文/王兆荣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六日,九十七岁高龄的陶博吾先生在南昌与世长辞,乘鹤西去,结束了他那无比沉重的一生。葬礼极其简朴,诚如他一生为人。
西山墓地,翠绿簇拥,怀恩寺后,一丘红土覆盖着这百年孤独的灵魂。墓碑两旁,刻着他生前为自己写的两幅挽联,苍凉,悲壮,在风中仿佛还听到他在沉吟,在叹息:
智既不能,愚亦弗及,碌碌庸庸天地苍茫何处去;
生无可乐,死又奚悲,悠悠忽忽飘流魂魄断归来!
尝遍苦辣酸甜,几番东扑西颠,浊骨敢追超脱者;
历尽风霜雨雪,纵使千磨万折,黄泉不作可怜魂!

我与陶老为莫逆交,廿年来肝胆相照。陶老走了,留给我的是无穷的思念,我曾以“孤独而又灼热的灵魂”为题,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以此为这位“一生不识长安道”的“栗里后人”送行。
先生名文,字博吾,别署白湖散人,一九00年生于江西彭泽县。彭泽背靠庐山,面临鄱湖,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先生少年时即聪慧过人,诵唐诗宋词,皆过目不忘。六岁入私塾,得秀才周载西启蒙。九岁从乡贤周介藩读四书五经,十岁通音律。稍长,即以诗作鸣于乡里。十四岁时与本县六位老先生组建的“六雅堂”诗社唱和。常以诗文评击时事,在县里逞才使气,颇有影响。
少年得意的陶博吾并不满足于此,决心赴大城市深造。一九二五年考入南京美专,从沈溪桥、谢公展、梁公约等为师。后因战事骤起,中途辍学。一九二九年,年近而立之年的陶博吾,终以优异成绩又考入为弘扬吴昌硕艺术而创办的上海昌明艺专,直接进入二年级。昌明艺专师资雄厚,国画教师有王一亭、黄宾虹、潘天寿、诸闻韵等;诗词课由前清翰林、著有《梅花诗集》的著名学者、儒医曹拙巢老夫子担任。陶的诗书画课成绩均在同窗之上,在校时,就有“诗人”之称。
昌明后期,又与林散之为先后砚友,立雪黄门,师事宾虹夫子。黄宾老视陶文如子侄,师生朝夕相处。黄老学识渊博、功力深厚,收藏又极富,是海上名宿、一代宗师。听夫子纶音,观夫子挥毫,使陶博吾眼界大开,学业大进。昌明一段岁月是金色的,昌明诸师博大的胸怀,精湛的技艺,高尚的人品,对陶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陶博吾当时最崇拜的是吴昌硕先生,进昌明时,吴昌硕已过世二年,未亲受缶老教诲,每念及此,抱憾不已。缶老长子吴东迈与陶博吾交往甚密,数十年书信不断。《缶庐集》问世后,吴东迈即将此集寄陶博吾,陶爱不释手,随即赋诗一首以回报:“缶翁生性自孤屼,缶翁之气更郁勃;诗卷长留天地间,旷逸纵横有奇骨。嗟余读书生苦晚,仰止之情空款款;遗集寄我千里来,开卷窗前春风满,人生何事日相逐,秋月春花易反复;但愿天地长清肃,白云四围三间屋,修竹丛中日日读。”
昌明毕业后,何去何从?陶才华出众,本可留校任教,或在上海另谋一个更好职位,这皆非难事,几年后,即可跻身海上名流行列。且当时又有一位同窗女生曹文杰,是才貌出众的千金小姐,愿以身相许。大都市张开臂膀在等待他的投入时,他却戛然而止,毅然抛弃眼前一切机遇,只身回彭泽故里,归隐田园。世态炎凉、宦海浮沉、功名利禄皆过眼烟云,他宁愿过那乡间的生活,三间书屋,千竿修竹,白鹅湖上泛舟,乡间小路上独自漫步……他与大自然有解不开的情结,继续去做那历代文人反复去做的、却又永远实现不了的桃花源梦。
从今天看来,文人操守,养性修身,洁身自好,均无可非议。但是否要归隐,逃避这一现实,去归从另一现实?他的归隐情结是为了寻找精神家园,是大彻大悟后的人生风范,并非故作姿态,去效仿终南捷径。黑格尔当年也那么固执,宁愿去偏远的乡村当个家庭教师,也不愿跻身热闹的文坛。
旧中国的现实是找不到理想王国的,陶博吾回归故里,也仅只过了几年怡静、闲适的生活。之后几十年,直至1980年中共三中全会前,他一直东扑西颠、饱经沧桑,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中国文人无法逃避那苦难深重的中国现实。那难以摆脱的忧患意识,那对祖国、对人民欲罢不能的爱恨情怀,必将伴随他们的一生。陶博吾是个道地的中国文人,在人格上他不断自我完善,在精神上、在肉体上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种种磨难,诚如中国历史上许多正直、爱国的文人一样。
如果我们跟踪他一生足迹,细察和体会他那漫漫旅程中为我们留下的一切,不无遗憾,又不能不相信,他在精神上、肉体上经受那么多困匝和磨砺(这一切并非情愿,更不想再重复一次),与他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又是那么难以分开。没有这些经历也就没有今天陶博吾其人和他那苍茫凝重、含浑无尽、至大至刚的诗书画艺术。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阴差阳错,千磨百折,孤独寂寞,反而造就了一个杰出的灵魂。
一九三一年,陶博吾回彭泽,筑“吾园”书屋三间,与孤松做伴,修竹为邻。他以教书为生,养家糊口。学业上继续得前清翰林许之静点化,得闲时游山玩水,吟诗作画,以文会友。其间作诗百余首,作画百余幅,书法习作就不计其数了,并常以诗书画习作与历代名家比,摹其墨迹,追其神韵。
“兴来畅泳三江水,醉倒横眠五老云。”
“浊酒何妨邀明月,菊花须插满头归。”
“长与疏篁作比邻,闲看群芳竟承宠。”
……这些诗句都是当时他舒适、闲散、超然生活的写照。然这牧歌式的田园生活,只是苦难深重的旧中国那漫漫长夜中的一瞬春梦。
日寇入侵,祸从天降,顷刻间,桃源梦破灭,他从此踏上流亡路,浪迹他乡。其间兵荒马乱,饥寒交迫,几死者数也。有诗记曰:
“地僻人荒无药处,亡家有泪任沉浮;
梦中颠倒难为鬼,枕上呻吟未报仇;
云影低笼连屋暗,泉声乱响寒流逼;
妻儿岂必频频泣,何处青山非故丘。”
民族遭此劫难,陶先生痛心疾首,愤然命笔:
“门前松竹虽自绿,江山不是旧山谷,
故都文物任践踏,同胞万人尽杀戮;
有田不敢耕,有家不敢宿,
江山如此谁倩牧,月里唯闻鬼夜哭。
此仇此恨何时雪?漫对山河空凄绝。
男儿宁为雄死鬼,赤血丹心不可灭,
愿得全国之人赤血丹心不可灭,
倭奴,倭奴,
我将食汝肉而饮汝血,
戴天之仇才可雪。”
另一首诗写道:
“纵马驰驱辞故土,扬鞭慷慨赴疆场,
此行不饮倭奴血,誓死黄河古道旁。”
…陶先生这近百首声声泪、字字仇的诗篇,表现了他凛然的民族气节和炽热的爱国情怀,国难当头,热血沸腾,慷慨悲歌,借激扬文字浇胸中垒块,一扫过去凄婉清丽、隽永飘逸的诗风。
当我们对陶博吾一生著作进一步探奥时,不难发现,成就中最重要、最突出的部分都是在八年抗战、十年“浩劫”那最苦难、最屈辱的日子里写出来的,许多“恒发于羁旅草野”的“是故文章之作”,许多悲愤难抑的不平之鸣,是他一生作品中最闪光、最有历史价值的部分。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流亡路上,船泊吉水县境三曲滩。一日夜,九江一妇人,在船舱夜产一子,病不能养,翌日舟行,竟弃儿于沙滩不顾。同舱难民初斥妇人无情,舟行后,见妇人气息奄奄,复与妇人同泣,江水载着一舱人眼泪以去。博吾目睹此情此景,悲愤难抑,仰天长啸,作《弃儿行》一首,以歌当哭:
“弃儿沙滩上,儿哭母更哭;
哭声一何悲,舟行一何速,
一村复一村,青山罩白云,
遥遥道路远,儿哭母不闻。
月光如水水如天,荒江寂寞秋风遍;
儿饥儿冷无人知,儿死儿生何由见,
儿生或有人悲悯,儿死勿怨母心忍,
母命瘦如柴,母苦血已尽,
故乡焚烧不能归,逃亡满地烽烟紧,
弃儿常已矣!痛心何日止,
轮回如有再来时,愿儿勿生干戈里。”
这首近乎白话的诗篇,每一句每一字都令人悲愤心酸,读罢撕人肺腑。陶博吾写这首诗时,稿纸为泪水所湿,诗成后,真不知其为泪为诗也。这首诗由于偶然机会,在当时民国日报上发表,后全国各家报纸都做了转载,成了当时一首有名的爱国诗篇。有人评论说,当与杜甫《三吏》、《三别》、《哀江头》、《哀王孙》等名篇相提并论。
浩劫十年中,在那“欲死不能,欲生无望”,“一家四分散,六口五饥寒”,“饥寒包瘦骨,污浊罩灵魂”的屈辱日子里,这位七十老人,箪瓢屡空,一无所有,过着非人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仍为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忧心忡忡,还不时地以诗文给别人以同情,给现实以清醒。仍然相信黑暗终将过去,光明会再来,并在诗中预示奸臣、逆贼的可耻下场,写下了诸如:
“……生祠莫学魏忠贤,雄风绞索死,臭骨没荒烟。”
“……擦亮两眼横高阁,看尽残暴恶毒人。”
“我来独倚瓦宫阁,坐看千帆破恶风……”
等正义感、是非观非常鲜明的诗篇。

(懒僧图)
1989年“陶博吾诗书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中有一幅用沉郁苦涩、雄强跌宕的行书写的《满江红》词一首,许多观众争相传抄,启功、李可染、周谷城等也无不为之感叹。
“豪杰英雄,有多少自夸无敌,君不见,投鞭淝水,赋诗赤壁,得意螳螂漫过喜,忽来黄雀逃何及,笑人生,千古总如斯,秋风急。 长城筑,销戈镝,阿房毁,坑降卒,想回环祸福,空留陈迹,胜败输赢原是梦,刀兵杀戮曾无极,只可怜苦了小黎民,年年泣。”
是何等沉痛、何等凄婉悱恻。回顾古今的“满江红”,因地位不同、境遇不同、视角不同,词的立意、境界也就不同。陶先生处于最屈辱地位,但在精神上、人格上独立自尊,这个孤独无依的灵魂积愤难抑,偷偷填句,可见其胆识。启功先生当年面对这首词说:这首“满江红”可以拿桂冠,要是前几年又会戴上“和平主义”帽子了。
陶博吾先生有着天生的诗人气质和世少其俦的传统学问功底,以及那及时捕捉、及时表达的非凡能力。当我们今天读他的诗,亦能感觉到他当时是在何种状况、何种情绪下写出来的,仍能感受他的心在字里跳,血在行间流,生命在诗里跃动,感情在诗里回荡。他熟谙历史,精通音律,灵感来时,激情如喷泉一样,炼词造句又是那样精确,那样富于情趣。在精神家园和艺术王国里他自由、充实。他不因功名利禄而累、毁誉与否伤神,亦无世俗人情缠身,从不为作品能否展出、能否发表获奖而去苦恼,有人赏识、无人赏识对他来讲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自己是否满意。他作书从不写别人的句子,作画从不题别人的诗文,得意也好,失意也好,皆自作诗文聊以发抒。如此高昂之风骨又如此峭异之才情,这绝非一般轻薄浮夸、沽名钓誉之辈所能望其项背的。
陶博吾先生的诗文、楹联、随笔和其他论著以及他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谈话录,至今很少披露,有朝一日公之于世,我相信其思想和艺术价值会有公论的。如果不带偏见客观地去看,仅就诗词而言,它的思想深度、文化内涵、人格力量,特别是对时代的批判精神,近现代许多书画大家恐都难以与他相比,即便是历史上许多谙于诗道的文人画家也难企及。
陶先生的书法艺术,其学书过程与古人无多大区别,究其渊源,与传统一脉相承,青少年时遍临百家,转益多师。他潜心传统,优游法度。中年以后,得益于昌硕大师的影响,宾虹夫子的教诲,驱遣百家,机参造化,于石鼓文、散氏盘铭文的研究中攻坚突破。在长期的临池实践中,又能深思敏悟,取精用宏,使胸中的感情起伏与纸上线条的运动达到高度默契,遂自成家法,独立门户,百年的苦心经营,终垒造了自己的山头,以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风骨雄踞当今书坛。
陶博吾真、草、隶、篆皆擅长,尤以行草、大篆更为突出。乍观其行草,枯葛峻峭,诙谐幽默,甚至歪斜扭曲,荒诞奇谲。在时人眼里,似乎不够纯正优美,不够雍容华贵、不入时尚、不合法度。“书如枯葛形尤丑,诗比村醪味更酸”(陶博吾联句)。他的书法确实很难用某种尺度去衡量。他对形式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既承认并崇敬书法艺术古典形态的崇高和典雅之美,又对古人、同辈及后学的创造均很尊重,他的书法只属于他自己。他推崇宋代尚趣的书风,对于倪瓒的萧疏、青藤的狂怪、八大的冷峻、傅山的丑拙等等一切有个性的书风和一切有独特见解的书论他都很欣赏、推崇。如傅山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书论,他常常谈起,并自认他的实践比傅山走得更远。他追求和向往的是天真率意、稚拙古朴顺乎天倪的,既不失传统规范又有现代意识的大美、大巧。
陶先生作书时心态全然放松,无须矜持。他不受千古不变的法度技巧的束缚,任其纵横交错,自由舒展。从这些夸张扭曲、结体俏皮的作品中,仍可看到汉时的峻峭、北魏的刚劲和宋元的情趣。有时像蟠螭老松,苍劲老辣,有时又像孩儿歌舞,天真烂漫。细细品味陶老许多成功的作品,既有古典艺术令人神往的魅力,又有令人惊异、使人感到陌生、又感到新鲜的现代审美情趣。
陶先生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不可能脱离民族文化传统大的审美范畴,对于外来的西方文化了解甚少,亦可说无心去领略,对于“现代派绘画”、“现代派书法”很难苟同。但陶博吾的书法、绘画,还有一部分恣意纵横随着意识流自由徜徉的文学随笔,为何又自然地流露出很强的现代审美情趣?对形象的塑造和形式的发现,有意无意地又存在着现代审美视角。这主要是他倔犟的性格——那百年风吹雨打被扭曲了的个性,在艺术创作时能充分而又自由地得到表现,又因为他有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生活境遇,如此众多的苦难,在心灵深处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在创作过程中那孤兀的灵魂悲怆的叹息、呼叫,曲折地被反映在作品中。他主体意识又极强、直率地流露心迹,无所顾忌,自觉地根除传统和时尚的束缚,一意孤行,故他的诗词、书法和绘画,既不同于古人又不同于现代其他人,体现了他的进取和异端精神。不难理解,他的书画与现代艺术有许多契同之处。由于他的特殊性,又决定了他的艺术有不可重复性。
再看陶博吾的大篆,以石鼓文集联、散氏盘铭文集联为其代表作,集中反映了他在篆书上承前启后的成就。篆书的书写不再只是表现字形的准确和功力的大小,个性和情感的表达上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其石鼓文集联和用石鼓文字形演变的其他作品无疑是师承吴昌硕的,得乃师的风神骨力,但又有自己的创造,用启功先生的评语来说:“在生动、随意、趣味、变化方面比吴缶老略高一筹。”
李可染先生观看他展览时也有类似的看法。但石鼓文的研究毕竟还是吴在前、陶在后,即使有创造,那也只是丰富和发展了吴派艺术,当然,能在吴昌硕基础上有所发展这已经不简单了。然而在散氏盘的研究和创作上,他却有着更多自己的独特创见,更能体现他的功底和胆识。
他在散氏盘铭文生动变形、稚拙古朴的基础上,再加以夸张,解体、变形、走极端,并掺以草法、随意性,给这古老的文字艺术注入了现代活力,使之结体更加自由舒展,字形更加跌宕奇特。局部放大来看,笔画的摆布,行间的阵势,空间的构成,似若不经心然又经心之极,令人叹为观止。在运用有限的文字集成联句,无人与他相比,陶先生能将这五百余字的石鼓文(其中还有许多重字、死字)集成九十九副楹联,那字数更少的散氏盘文也集成了八十余联,而且每联均工偶对仗,含意深长,毫无牵强生硬之感(这两集楹联已出版)。无深厚古典文学功底,无丰富的历史知识,恐难有此创举。
陶先生还是一个文字学家,致力于小篆研究,有《小篆研究》三卷。因其著作已结集出版,自有公认,不再赘述。

(五老图)
由于陶先生的诗名、书名而掩盖了画名,他是我国老一辈科班出身的艺术家,在南京美专、上海昌明艺专打下了深厚的传统笔墨、造型和理论基础。在名师指导下,对中国画传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近溯远地学习、领悟,不仅得古人画理、画法的精髓,并得古人之心,进而“默契造化,与道同机”,得自然之钟秀灵气,使他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进行变法、创新时,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生活基础。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很难找到那脱离生活、凭空臆造的痕迹。在艺术表现上诚如诗词、书法一样,特别注重的还是独创精神。
在为人处世上,他是一个宽厚随和的老翁;在艺术表现上却是一个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狂放不羁的怪才;他有意要与传统和老师拉大距离,不与人同,不随人后,不落俗套,不入时尚。过去以为在吴昌硕的学生中,跳出吴昌硕的只有一个潘天寿,现在看来还有一个陶博吾。
他的绘画题材多取之于山林荒野和日常所见的花鸟蔬果,与大自然怡然契合。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景物,到他画面上却出现不同凡响的效果,形象夸张怪异,拟人化、比喻性,这些艺术形象,都与真实形象相去甚远,似又不似,不似又似。野兽派大师马蒂斯说过:“只有当他忘掉一切他所见过的玫瑰,他才能创造自己的玫瑰。”他画面上的形象是他自己人格、志趣、个性的体现。因为有书法的功底,线条的驾驭能力又是那样得心应手,又因为他是个诗人,每幅画上皆自题诗句,有时先有诗后配画,画面上充溢迷漫着诗的意境;有时先有画,后题诗,诗的配合,把画的境界加深了、扩大了。诗书画熔一炉,互相辉映。
再看陶先生的感情世界,这棵蟠螭斑驳的百年老松,饱受人间的苦难,一生中特别看重的是人间的真情。
陶先生对他的母亲无限情深,每当谈起母亲,会像孩子一样哭泣,直到90多岁高龄还是如此。那年轻时的已经非常久远了的一段旧情,缠绵悱恻,系绕他一生。
当年那位彭泽县高小女校长张肖梅,这位出身封建大家庭、并受过高等教育的才女,仰慕他、钟情他。当她无法摆脱封建礼教的婚姻,追求不到新生活时,竟为陶博吾徇情而死。从这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世纪末,陶先生走遍庐山脚下的星子县,决心要找到她的坟茔,要去哭一场,要为她写块墓碑,要与她合葬,以此了却这段情。
五十年代,一位同在中学里执教的同事曾景,牢骚太盛,不满现实,终锒铛入狱,妻子跑了,亲友皆远离避嫌疑,陶先生虽囊中羞涩,但对落难同事从不间断地给予接济,这位傲气十足也曾显赫一时的前云南师范学院院长每天收到他送来的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时,总是号啕大哭……
人间还有许多真情他都想还,浩劫后,那位在职时曾百忙中为他排难解忧的南昌市长下台后,门前顿时冷落,时已八十多岁并患有严重白内障的陶博吾,带病执杖摸索着找到他家门,秀才人情纸半张,送上一副对联:“多栽翠竹摇清影,独上高楼看远天。”
“杜鹃牡丹一丛丛,谁忆深山老劲松?”
“彭泽已无人,更有谁怜孤影?”

(携幼寻梅)
有时他也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似乎也在期待着什么。陶先生无意要成为诗人、书家、画家,更不想跻身名人行列,这个偏远省份的、以教书为终身职业的一介老书生,远离名利,不求闻达,怀着平常心,过普通人生活。但百年之中的苦难总是跟踪他、折磨他。经过千磨百折,最终又成为诗书画大家。如果条件好一些,机遇来得早一些,或许成就远非现在这个高度。无涯惟智,即便如此,陶博吾以他的人品艺迹,已经建造了一座与众不同的丰碑。
一九九五年秋,九十六岁的陶老亲自从南昌赶到上海,参加“陶博吾诗书画展”开幕式和研讨活动,他辞谢任何招待和张扬。风烛残年,身已佝瘘,对于这位经受百年孤独的盛世遗贤,上海的一些著名学者、教授、作家、书画家向他表示了由衷的致意:
蒋孔阳先生称他是现在重新被发现的一位对时代有批判的现实主义大师;白桦先生称赞他有三个不朽:生命的力量不朽,智慧的力量不朽,艺术的力量不朽;赵冷月先生激动不已,说他这一辈子最崇敬的是陶博吾这样的书家;旅美油画家陈丹青捧读他的诗集,爱不释手;戴厚英送上自己的文学作品,当面聆教,并撰文“贡献一个人”在文学报上发表。一位书家感慨地说:“陶博吾现象的出现,对二十世纪中国书法来说是一种荣幸”;另一位书家说:“想起这百年孤独的老人,总忍不住要哭一场。”
陶老对此只有一句话:我的东西还不成熟。
诗人已去,“松菊犹存”。他把爱和恨都留在作品里,这个“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老人,是一本太沉、太厚的书,篇终又接混茫,它的深度、高度远非笔者所能论述得透彻的。
君不见,民族文化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源远流长。谁能汇入进去,谁就将得到永存。此集的出版,实现了陶先生最后的愿望。并以此集的出版纪念陶博吾先生100周年诞辰。
(本文作者:王兆荣1941年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承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先生。曾任江西省文联副主席,江西书协常务副主席、秘书长,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上海吴昌硕研究会副会长。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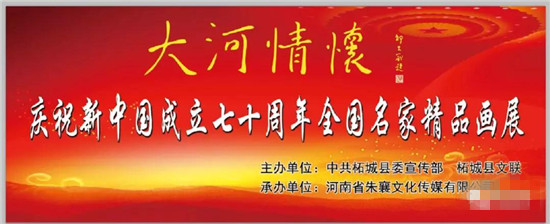 【潘建博】大河情怀—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潘建博】大河情怀—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一路南方即将在798艺术区作者画廊开幕
一路南方即将在798艺术区作者画廊开幕 贝因美科学育儿全国巡回公益讲座启动
贝因美科学育儿全国巡回公益讲座启动 异态灵体的狂想- -张弛个人作品展在北京虹
异态灵体的狂想- -张弛个人作品展在北京虹 悲情之目-陈蒙艺术个展即将开幕
悲情之目-陈蒙艺术个展即将开幕 张静:“日常治疗”展览开幕现场回顾
张静:“日常治疗”展览开幕现场回顾 “妙法庄严”姜雪雁佛教绘画艺术展暨世界巡
“妙法庄严”姜雪雁佛教绘画艺术展暨世界巡 边程《蜀山战纪2》将播 少年萧琅鲜生
边程《蜀山战纪2》将播 少年萧琅鲜生 黄俊鹏居家写真曝光 霸道总裁换装独
黄俊鹏居家写真曝光 霸道总裁换装独 侯佩杉《龙日一》今日收官 美龙cp喜
侯佩杉《龙日一》今日收官 美龙cp喜 “动次元” 偶像组合地球护卫队Odyss
“动次元” 偶像组合地球护卫队Odyss 陈赫前妻许婧感慨:放弃往往会得到更
陈赫前妻许婧感慨:放弃往往会得到更 彭于晏最新大片曝光 街头感十足
彭于晏最新大片曝光 街头感十足 郭富成4月18日大婚 岳父称是听女婿的
郭富成4月18日大婚 岳父称是听女婿的 54岁温碧霞红装秀美肩亮相 与朋友玩
54岁温碧霞红装秀美肩亮相 与朋友玩 白百合“出轨”?陈羽凡不语?暗示两
白百合“出轨”?陈羽凡不语?暗示两 战狼破14亿,有望成为国产片的票王
战狼破14亿,有望成为国产片的票王 张杰:只有你让我每天笑着醒来
张杰:只有你让我每天笑着醒来 高考在即 王俊凯暖心祝福易烊千玺:
高考在即 王俊凯暖心祝福易烊千玺: 儿女齐聚为贝克汉姆庆父亲节 小贝搂
儿女齐聚为贝克汉姆庆父亲节 小贝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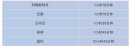 伦敦再添中餐厅,住在金丝雀码头的你
伦敦再添中餐厅,住在金丝雀码头的你 美对俄制裁法案再遇阻 石油巨头担忧
美对俄制裁法案再遇阻 石油巨头担忧 莉莉-柯林斯登美国《Shape杂志》封面
莉莉-柯林斯登美国《Shape杂志》封面


